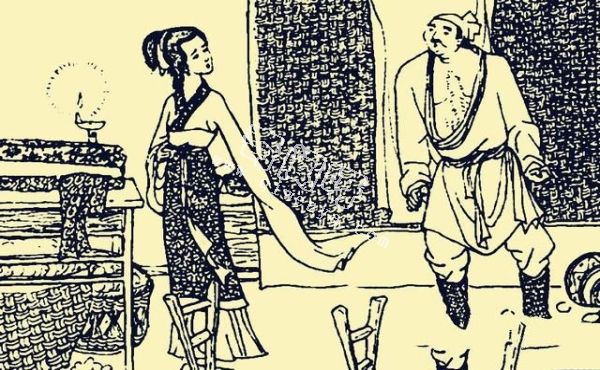一、突现尸块
近日张怀圣偶感风寒,病卧在床,全仗刘庆和严参端水熬药地照料,身体却没见好转。这天,事情却找上了门来——应天府尹求他去破一件案子。
张怀圣本不想帮忙,但应天府尹的一句话却让他不能不答应——这起案子就发生在城西教堂院墙之外,如果不能迅速破案,不但教堂圣地会受到玷污,甚至那些教父、修女都有可能被愤怒的百姓杀掉。
张怀圣自小在教堂长大,听说教堂有难,焉有袖手旁观的道理?于是强撑病体带上严参和刘庆,跟随着应天府尹赶到了教堂之外。
教堂周围已经被官兵包围,外围看热闹的百姓已经把教堂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。教堂的门窗都开着,里面的人都探着头往外面看,眼神里充满了惊恐。在教堂正门前面的大街上,扔着一个被打开的白布包裹,包裹的一角已经被解开,露出一片白花花的肉来。

现场已被践踏得一片狼藉,张怀圣嘱咐严参将包裹小心取走,送到刑部停尸房仔细勘验,自己则带着刘庆迈步进了教堂。
刚一进门,神父就冲上来抓住他的手说:“怀圣,今天这个案子,的的确确跟教堂没有任何关系,我们都是上帝的羔羊,怎么可能做出这种杀人分开的事来呢?你可一定要帮我们查个水落石出,不然,教堂里面这些人就要魂归天国了!”
张怀圣的神色非常凝重——在查看尸块的时候,他就已经听到了人群中的议论:这些尸块就是教堂里的人扔出去的,那些外国人表面上神色和蔼,可仔细瞧瞧就知道了,他们很多人身上的长毛还没褪净,骨子里的兽性还保留着不少,据说到了月圆之夜就会吃人!这些尸块,就是他们吃剩下扔出来的!京城要想太平,就必须把这些吃人的外国人杀死!
神父告诉张怀圣,昨天晚上教堂周围一直很平静,只是到了五更天的时候,教堂敲钟人曾经听到有马车跑过的声音,那辆马车围着教堂转了一圈,马蹄声很是刺耳。敲钟人跑到窗口查看,地面上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清,只能看到一盏红色灯笼在快速地朝东城方向移动。天刚蒙蒙亮的时候,外面就传来了尖叫声,有人发现了尸块,教堂也被愤怒的人群围了起来。
张怀圣转声唤过刘庆:“胖子,这件事还得麻烦你,这京城地界,几乎没有你找不到的熟人,你出去顺着教堂往东城的方向一路找下去,看看能不能找到那辆马车的蛛丝马迹。虽然京城马车不少,但大早晨这么急匆匆赶路的却不多,沿着红色灯笼这条线索找下去,应该有所收获。”
刘庆点头答应,刚要走,应天府尹又从外面跑了进来,慌慌张张地对张怀圣说道:“张大人,不好了,刚刚接到禀告,东城药王庙、南城报国寺、北城神医堂的门口,又发现了尸块,包裹尸块的白布跟教堂门口的一样,我已经命人把所有的尸块都送到刑部停尸房。”
张怀圣心里暗暗叫苦——这个应天府尹只知当官,一点都不懂得保护现场,自己让严参把尸块带回去,是因为教堂外的现场破坏严重,已经没有察看价值,新出现的尸块的地方自己还没看,怎么就擅自处理了呢?
他转头看了看刘庆,说:“情况有变,你要先去东城门,然后倒着往回找,直到教堂,把马车行走的路线找出来。”
他又对神父说:“我自小在教堂长大,敢肯定尸块绝对跟教堂的人无关,不过现在外面比较危险,您让教堂里的人没事儿不要外出,应天府尹暂时不会撤去兵丁,待破案之后,一切危险自然就会烟消云散的!”
二、鬼魂驾车
从教堂里出来,张怀圣径直去了刑部的停尸房。停尸房里,严参正对着四个包裹发愣。张怀圣定睛一看,身上的汗毛都立了起来——看得出来,这四包尸块分别是人的两条胳膊、两条腿和胸部、腹部的尸肉,切割的刀口非常光滑,没有骨头,但骨头上原有的筋络都割了下来。
严参指着尸块说:“大人,我在刑部供职多年,勘验过的尸体不在少数,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分开的,所有的刀锋都是顺着肌肉和骨骼的纹理走,没有一丝一毫割错的地方,手法之高令人咋舌。我记得《庄子》中曾经有过‘庖丁解牛’的记载,厨工在宰牛的时候,能只凭着感觉就能将牛肉和牛骨分开,牛肉能像泥土一样散落下来,我一直以为这记载是在夸张,可今天看来,这个分开人的手法,并不亚于那个庖丁!”
张怀圣听了连连点头,又问严参:“那依你看,就凭这几块尸体,能不能找到此人身份呢?”
严参点点头,指着尸块内侧说:“大人请看,这肌肉纹理里的血丝,都已经成为黑色的了,而切割的边缘并没有血流下来的痕迹,说明分开人在动手的时候,尸体至少已经存放了五六天,血早已凝固。尸块表面并没有伤口和淤青痕迹,估计并非横死,再看尸块表面,毛孔周围还能看到有些黄土的微粒,说明这具尸体并没有装棺,而是光着身子埋在土里的,连张苇席也没用。这太不正常了,因为从这些尸块上来看,死者应该比较胖,最起码吃穿不愁,这样的人家,怎么会让自己人光着身子埋在土里呢?所以,据属下判断,这个人其实并没有下葬,而是在等着复活!”
“等着复活?”张怀圣不由一惊,“你是说这个人当时并没有真死?”
严参告诉张怀圣,在北方,每到冬天,总有人家烧煤取暖时不慎,煤炉漏气导致中毒将人熏死过去的案例。名医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曾有记载“人有煤气中毒者,昏瞀至死”的说法。民间传说治疗煤气中毒最好的方法,就是在野外挖一个土坑,将中毒之人衣服褪去,全身埋在土里,只将头部露出,七天之内,有的人可能苏醒过来,醒不过来的,再发丧埋葬。而这具尸体在煤气中毒之后,应该已经死了,家人按照民间传说进行治疗,结果尸体被人盗去分了尸。因此,只要在城中寻访一下,看谁家的汉子中了煤气之毒,治疗时尸体又丢了,自然就找到尸源了。
张怀圣冲着严参竖起了大拇指——说心里话,他对民间的这种风俗真没有严参知道得多,现在就好办多了,按着严参的主意去找,应该不会太难。
还没等张怀圣派人出去查问,就已经有人找上门来了。来者是个三十几岁的妇人,她说自己家住西城贾家巷,丈夫是个杀猪的屠夫,叫霍进财。七天前的晚上,霍进财喝多了酒,打了她一顿,吓得她跑到邻家躲避了一宿,谁知第二天一早起来回家,发现霍进财口吐白沫躺在炕上一动不动了,邻居中有见识广的,猜出霍进财是煤气中毒,这才在城外挖了个坑,将霍进财的身子用土埋住,在旁边搭了个席棚,雇霍进财的好朋友杜猪儿照看。谁知今天一早,杜猪儿跑回家来报信儿,说霍进财的尸体不见了。霍家上下乱成一团,听说教堂这边出了分开案,于是赶紧来认尸。
张怀圣将霍氏拦在了门外,问她丈夫身上可有什么明显的标记,霍氏想了想,说霍进财日常杀猪为生,左小腿肚曾被猪咬过,留下了一个贯穿的伤疤。张怀圣朝屋里的严参看了一眼,严参点了点头,张怀圣闪身让开,让霍氏进去查看,霍氏进入停尸房没多大工夫,就哭起来。
张怀圣和严参劝了半天,好不容易把霍氏送走,刘庆就从外面气喘吁吁地来了。进了门,他得意洋洋地拍着胸脯说:“张大人,我老刘出马,一个顶俩,已经知道驾着马车抛尸的人是谁了。”
张怀圣急问:“是谁?”
刘庆腆了腆大肚子,说:“我按照大人的吩咐,顺着东城门一路打听下去,果然沿路不少人都听到了马车路过的声音,而当追踪到东城门的时候,城门口卖烧饼的摊主告诉我——今天早晨城门刚开,的确有辆带着车篷的马车出城,坐车的人不知道是谁,但驾车的人他认得,正是西城屠户霍进财!这个霍进财我听说过,是个杀猪卖肉的高手,杀猪的时候,一刀毙命,猪都感觉不到疼,卖肉的时候,要多少一刀准,多了白送,少了双倍赔偿……”
刘庆说得天花乱坠,却看到张怀圣和严参像看怪物似的看着他,不由闭上了嘴巴。张怀圣轻轻哼了一声,说:“你说的那个霍进财,全身的肉都在这儿,他是怎么赶着马车出城的?莫非你看见鬼了?”
三、找到凶器
张怀圣话音一落,刘庆那张胖脸顿时涨得通红——东城门卖烧饼的摊主是他多年的朋友,绝对不会欺骗他。也正因如此,他才急急忙忙跑回来告诉张怀圣,他转身想再去东城门,张怀圣拦住了他——马车出了城就如同泥牛入海,再想找可就难了。眼下还是先去霍家看看,看霍进财是否得罪过什么人。
三个人换了便服,直奔西城贾家巷,快到巷子口的时候,张怀圣突然拉了严参和刘庆一把,三个人躲到墙角,只见霍氏正低着头急匆匆地从巷子里走出来,朝另外一条巷子走去。
张怀圣和刘庆严参在后面悄悄跟随,只见霍氏走过了几条巷子,来到一座破败的宅院跟前,四面看看没人,推门走了进去。
三个人蹑手蹑脚地走到了房子的后面,只听里面传来霍氏和一个男人的说话声:“赶快把银子还给我!”
那个男人的声音有些色眯眯的:“什么?要银子?你什么都不给我,我凭什么给你银子啊?嫂子,来吧,小弟我惦记你好几年了,要不是怕你家那个凶神恶煞,我早就跟你……”
随后又传来了霍氏的声音:“你这个畜生,我那个死鬼不在了,我迟早是你的人,急什么?对了,你先把欠我丈夫的那二两银子还给我,我料理完了他的后事,才好再嫁!”
屋里的男人笑道:“我没欠你丈夫银子,倒是你欠了我一笔相思债!来吧,让我亲热一下……”
屋里传来霍氏的一声尖叫,刘庆早就按捺不住了,腾身一脚把后窗踢个粉碎,一个鹞子翻身蹿了进去。只听屋里咚咚两声,随即传来了刘庆的喊声:“大人,进来吧,人已经被拿下了。”
张怀圣绕到前门,进了屋,只见屋子里一片凌乱,霍氏的衣领已经被撕开了,再看地上躺着的那个男人,只穿着贴身的衣服,两只眼睛又青又肿。张怀圣看了看霍氏,又瞅了瞅地上的男人,说:“孤男寡女,独处一室,成何体统?”
躺在地上的那个男人挣扎着站起来,冲着张怀圣连连磕头:“大人明鉴,小人名叫杜猪儿,也是肉市上的一个屠户。我对霍家娘子的确有些非分之想,但霍进财之死确实与在下毫无关系。刚才我刚要躺下睡觉,霍家娘子就进来了,想到她丈夫已经不在了,小的才临时起意,做了这等下作之事。”
霍氏扑通一声跪在地上,说:“大人,他在撒谎!刚才,他让个小童儿到我家送信儿,说他欠我丈夫二两银子,送过来怕夫家的人和我争抢,故而让我亲自来取。没想到,我刚一进门,他就想……”说完,霍氏嘤嘤地哭了起来。
杜猪儿一听霍氏的话,差点儿蹦了起来:“大人,这霍家娘子满口胡言,她家相公虽然和小人同为屠夫,可小人的银子都是靠手艺挣出来的,从牙缝里省出来的,而她家相公却每日喝酒赌钱,我怎么会欠他的银子?再说了,我到现在还没起床,怎么会派小童儿去她家送信儿?摆明是诬赖好人啊!”
张怀圣冷冷地看了杜猪儿一眼,说:“你到现在还没起床,是不是昨天晚上干了什么事儿睡得太晚?”
杜猪儿愣住了:“大人容禀,自打霍进财被煤气熏过去之后,霍家娘子就雇小人在城外野地照看他的尸体,小人一连看了五六天,昨晚有些倦了,眼看那霍进财的脸都已经开始风干了,怎么也不可能活过来,于是就找了地方喝酒去了,半夜才回到席棚睡觉。早晨起来撒尿的时候,才发现霍进财的尸首不见了,于是赶紧去告诉霍家娘子。这事儿都有人证,小的不敢撒谎!”
张怀圣哼了一声:“人家花钱雇你看尸体,你给看丢了不算,居然跟没事儿人似的在家睡大觉,还要调戏死者之妻,该当何罪?”
正说着,严参从外面向张怀圣招了招手,张怀圣走了出来,只见严参用手指尖捏着一把剔骨尖刀,小声说:“大人,这是在他家柴房里找到的,在刀旁边的柴棒上,还有一小片肉,我仔细看过上面的毛孔了,跟胸部尸块上的非常相似。”
张怀圣点了点头,让严参把刀和肉片放好,随即命刘庆把杜猪儿捆了,让霍氏跟在后面,一起带回了刑部。
四、再生枝节
到了刑部,严参拿着那口刀和那片肉去了停尸房,张怀圣则让刘庆上街买来一大块带骨的猪肉,要杜猪儿当着三个人的面把骨头上的肉剔干净。张怀圣告诉杜猪儿:只要他能把这块猪肉剔得骨上无肉,肉不掉渣,就可以免了他欺侮霍氏的罪过。
杜猪儿不明所以,听说只要把肉剔好就可以免罪,立即甩开膀子干了起来。你还别说,这小子的手艺还真不是吹的,刀随手动,手随眼动,眼随心动,不到一炷香的工夫,骨肉已经全部分开,果然是骨头上光溜溜,不见半点肉末,而分割出的猪肉也是齐齐整整,并没有肉渣掉下来。
张怀圣看罢,心里就已经有了底——这案子真不是杜猪儿做的。倘若是他做的,那让他剔肉的时候,马上就会想到这是在验证分开人是不是他,那他怎么还会拿出自己的真本事来?更重要的是,张怀圣发现杜猪儿在剔肉时,更多的时候是在用刀尖,所以肉虽然剔干净了,但切开的截面却有些坑坑洼洼的,而那些尸块明显使用了更多切的手法,截面非常光滑平整。
看张怀圣的面色有所缓和,杜猪儿试探着问:“大人,您说只要我能做到骨上无肉,肉不掉渣,就可免了我欺侮霍氏的罪过。小人都做到了,能放了我吗?”
张怀圣笑了笑,说:“我只说免了你欺侮霍氏的罪过,并没有说免了酒后丟尸的罪过!”
杜猪儿苦着脸说:“大人,酒后丟尸也算罪过啊?那霍氏虽说雇小人看守尸首,却并没有给小人工钱,连小人喝酒的钱都是自己掏的,要是因为这个治小人的罪,那可太屈了!”
张怀圣命严参取一包尸块过来,放在杜猪儿面前,告诉他这就是被他弄丢了的霍进财的尸体。杜猪儿看了一眼尸块,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,过了一会儿,他才醒过味儿来,朝张怀圣连连磕头求饶。张怀圣哈哈一笑,让他自己辨认——整个京城内的各类屠夫,不管他是杀猪的、杀牛的、杀羊的还是杀驴的,究竟谁能有这么精妙的刀法,找到那个人,杜猪儿身上的嫌疑才能解除得干干净净。
杜猪儿壮着胆子靠近尸块,仔细看了好长一会儿,摇了摇头,说:“启禀大人,依小的看,能这么分开的,绝非我们这等杀猪卖羊的人干得了的,天底下恐怕也只有一个人能做的了!”
“谁?”张怀圣瞪大了眼睛盯着杜猪儿问。
杜猪儿咧着嘴看了刘庆一眼,说:“只要这位大人答应不再打我,我才敢说。”
刘庆上前举起拳头,说:“我先打了你,你再说,如何?”
杜猪儿连连告饶:“能将尸体分得如此利落的,恐怕也只有《水浒传》里的专做人R包子的母夜叉孙二娘了!”
杜猪儿的话音还没落,早被刘庆一拳打出了一溜跟头,刘庆气呼呼地上前还要打,却被张怀圣拦住了。他吩咐把杜猪儿押下去,刘庆有些诧异,因为他看到张怀圣的嘴角上居然露出了一丝微笑。
这时严参来了,他告诉张怀圣,他刚才仔细观察了从杜猪儿家里找到的那片肉,发现和其中一块尸块有可重合之处,可以断定那块小肉片就是从霍进财尸体上割下来的,不过那把剔骨刀却和切割尸体留下的痕迹不同,最起码可以说明分开人用的并不是杜猪儿柴房里的那把刀。
张怀圣赞许地笑了笑,说:“老严果然是验尸高手,刚才我审过杜猪儿了,凶手并不是他,他说能有这样刀法的,只有母夜叉孙二娘!”
刘庆哼了一声,说:“张大人,那母夜叉孙二娘可是宋朝人,离现在已经有五百多年了,难不成你跑到宋朝去抓人?”
张怀圣颔首笑道:“稍安毋躁,我觉得这个分开人的面目已经慢慢出来了,他应该是个身材健硕、思维缜密的汉子,还非常自傲,谁都看不起。”
刘庆叹了口气,说:“大人,你不说鼻子不说眼,只说脑壳子里面的东西,这让人去哪里找?”
张怀圣摆了摆手:“我不用你画像,这个人已然模糊地呈现在我的脑海里。”
五、兵分两路
这时,严参忽然发现张怀圣的脸红红的,伸手一摸,额头都有些烫手了。他这才想起来,从早晨出来到现在,张怀圣已经有两顿药没喝了,本来他的身体就没有好,加上今天在外面跑了一天,病情又重了。
严参和刘庆忙拉着张怀圣回到照磨所,吩咐手下人赶紧点火煎药,看着张怀圣吃完药睡下了,两个人才回房。
第二天一早,严参和刘庆去看望张怀圣,张怀圣的病情稳定住了,他吩咐刘庆再去找东城门卖烧饼的摊主,仔细问问昨天看到霍进财驾车出城时有没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,然后再到另外三家出现尸块的地方查问一番,看有没有新的发现。随后,他又让严参去提审一下霍氏,问问她认不认识让她去杜猪儿家拿银子的小童儿。
下午,刘庆先回来了。他告诉张怀圣,自打知道了在城门口看到的那个霍进财已经被分开之后,卖烧饼的摊主已经吓得病了,说了一宿胡话,别想问什么了。没办法,他只好又去找其他人,有人告诉他,昨天早晨霍进财出城的时候,的确有些不太对劲儿,他驾车的姿势非常僵硬,脸上一点儿表情也没有,见到熟人也不打招呼,连最常用的“得、驾、喔”都不说。刘庆从这点猜测说,驾车的估计就是霍进财的尸首,只不过怎么挺直了驾车的,他暂时还没琢磨出来。至于另外三家出现尸块的地方,都没有发现什么,倒是在教堂外有了新发现——在一处不显眼的角落里,扔着几团脏兮兮的棉花。
说着话,刘庆把随身带回的一个小包裹打开,张怀圣撑起身子看了看,只见那团棉花共有六份,其中两份是长条状,四份则是团状的,几份棉花中间都压得薄薄的,有的还被泥水粘成了一团,边缘的地方还稍微干净一点儿。
张怀圣问:“刘庆依你看,这些棉花的蹊跷之处在哪里?”
刘庆说:“大人,马车在前三个地点丢尸块的时候,并没有人听到声音,再看看这些棉花肮脏的程度,我觉得马车的双轮和马的四蹄都应该是被棉花包裹起来的,到了教堂之外才弄下来丢掉。”
张怀圣点了点头:“你说得不错,赶车人在教堂外把棉花弄下来丢掉,而且还点起了红灯笼,最后在城门打开的第一时间出城,这个人时间算计得太精确了,几乎没有耽误一分一秒。”
过了一会儿,严参也回来了,他告诉张怀圣:霍氏说她不认识那个小童儿,只记得小童儿也就是八九岁年纪,长得白白净净,说话文质彬彬,也正是因为这样,她才会相信小童儿的话。严参在霍家四周打听了好长时间,也没有找到小童儿的踪迹。
另外,在审问霍氏的时候,严参还从霍氏那里问出了一个事情:她丈夫被煤气熏死过去之后,她首先求人把丈夫抬到了北城神医堂,可神医堂的大夫们并没有开药救治,而是让她把丈夫的衣服脱掉,在城外挖个坑,把头露在外面,身体埋上,说只有那样做,才可能活过来。她照吩咐做了,可一连几天丈夫都没缓过来。周围的人有的劝她到教堂祷告,有的劝她到药王庙求神,有的劝她到报国寺拜佛,各说各的,弄得她也没了主张,到最后干脆来了个病急乱投医,三个地方都去了一趟。
张怀圣听完,身子像被掏空了一样,咕咚一下躺在了床上。刘庆和严参都吓了一跳,赶紧过来扶住他。张怀圣摆了摆手,说:“没事儿没事儿,我就要想通了,分开人的庐山真面目应该快露出来了。”
六、意外惊喜
掌灯的时候,张怀圣喝了两碗粥就躺下休息,刚歇了一会儿,严参和刘庆走了进来。刘庆偷眼瞅了张怀圣一眼,说:“大人,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,琢磨案子是个费脑筋的活儿,如果不吃点儿好的,身子会垮的,来来来,这回我俩做东,酒是我从家里拿来的十八年的女儿红,菜是老严买的,正宗的呼家楼酱鸭,他买了两只,吃饱喝足发发汗,说不定明天你的病就好了。”
张怀圣摇摇头说:“我还是愿意吃清淡点儿的东西,你们俩在我这屋里吃吧,边吃边喝边讨论案子,说不定会碰撞出什么好主意来呢!”
刘庆拿起酒坛子,叹口气说:“唉,张大人,这可是真正的十八年女儿红啊,你不喝太可惜了。”
张怀圣微微一笑,说:“你一向喜欢在烟花丛中飞来飞去,能拿出十八年的女人红并不稀罕,只不过老严买的这呼家楼的酱鸭,估计好吃不了!”
严参一听急了:“大人此言差矣,这呼家楼的酱鸭乃是京城一绝,每日一出锅,人们都争着抢着去买……”
张怀圣笑了笑,说:“你既然知道人们都抢着去买,现在都到了掌灯时分了,你依然能买到,你想想,可能是真正的呼家楼酱鸭吗?”
严参挠了挠头说:“我平素没怎么买过东西,刚才胖子说让我弄个菜,我出门不远,就看见有人推着小车卖呼家楼酱鸭,于是就赶紧买下来了,当时也没考虑这事。”
看场面有些尴尬,刘庆赶紧打圆场:“管他是不是真正的呼家楼酱鸭呢,先吃了再说!”说完,他伸手打开纸包,拿出酱鸭,捏住一只腿骨,使劲儿往下一掰,谁知竟然把整个腿骨拔了出来,上面一点儿肉都没挂着。这下刘庆愣住了,他俯下身子仔细看了看,嘁哩喀喳把鸭子拆开,这才大声惊呼出来:“老严,张大人说得不错,你还真被人家骗了,这只鸭子是泥做的!”
张怀圣和严参凑近了一看,果然,这鸭子的头、脖子、脚都是完好无损的,但身子却只剩下一副骨架了,骨架间填充的全是软硬适中的黄泥,外面则包了一层酱黄色的宣纸,宣纸上又涂了鸭油,显得皱皱巴巴的,在夜幕下跟真的酱鸭没啥两样。
严参气坏了,起身就要出门找卖酱鸭的人去,刘庆一把拉住了他,说:“算了吧,人家好不容易把假鸭子卖给你这个冤大头,还会在原地等着你去找?”
这时,张怀圣却举着一副鸭子的骨架发起了呆,过了一会儿,他突然把鸭骨架一扔,也顾不得满手的鸭油,一拍脑袋说:“老严,还多亏了你买的这假鸭子,霍进财驾车出城的经过,我想明白了!”
张怀圣告诉刘庆和严参,分开案发生以后,他一直捉摸不透为什么明明霍进财已经死了,却依然有人看到他驾着马车出城。今天看到这鸭架,他终于想通了:其实那天坐在马车前面驾辕的,的确是霍进财,但并不是活着的霍进财,而是被分开以后只剩下头、脖子、手脚骨架的霍进财。他记得西方有一种技术,就是用熟石膏加水调成糊,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做成任何形状,而且很快就能变干变硬。分开人在将霍进财胸腹和上臂、大腿上的肉割掉之后,把石膏糊灌进霍进财的骨架,凝固后,霍进财的骨架就可以挺立住了。至于赶车出城,那就更简单了——霍进财在前面坐着,只是个样子,真正的赶车人其实躲在车篷里操控着马匹,出城之后,他把尸体藏好,又回到了城里。
刘庆和严参听得迷迷糊糊,修补残缺不全的尸体,中国大多采用木头雕刻、纸糊、黄铜铸造等方式,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三国演义说的孙权杀了关羽,把关羽人头送给曹操,曹操就命人用沉香木刻成躯体,与关羽的头颅一起厚葬,却从来没有听说过用什么熟石膏来修补的。
八、最后交锋
第二天天亮,早晨吃过饭,张怀圣独自一人出了照磨所,先到教堂转了一圈,然后直奔范穆尔的诊所。
范穆尔对张怀圣的到来并没有感到吃惊,一见面,他就问道:“张大人,病好些了吗?我正想去看您呢,您怎么来了?”
张怀圣摇了摇头,说:“范先生,我看你也别跟我绕圈子了,霍进财被分开这件事,就是你做的!”
范穆尔一听,哈哈大笑起来:“张大人,我回国三个月来,耳边听到的都是您破案如何神奇的故事,可没想到您破案的手段就是靠吓唬。而我在英吉利呆了十年,人家法律规定之严谨,破案程序之缜密,你们大明就是再追一百年,恐怕也难于望其项背。”
张怀圣冷笑了一声,说道:“范先生,你刚才这句话里,至少有三处错误:第一,我说分开这件事是你做的,是有根据的,绝非吓唬;二,你在英吉利呆了十年,回到大明才三个月,然后就判定英吉利在法律程序和破案手段上超过大明,这本身就不公平;三,你不应该说‘你们大明’,应该说‘咱们大明’。”
范穆尔被张怀圣说得哑口无言,过了好一会儿,他才干咳了两声,说:“那好,既然您觉得大明在法律程序和破案手段上不亚于英吉利,那就拿出证据来,只有铁证如山,我才肯承认,否则您就犯了诬告之罪!”
张怀圣不慌不忙地说:“我一直以为京城里有个非常厉害的杀猪高手,但审问杜猪儿的时候,他却告诉我京城里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人,而且他提到了一个人名——母夜叉孙二娘。要知道这个女人是专门杀人做包子的,这句话给我的启发很大,能够把尸体肌肉和骨架分割得如此漂亮的,必定学过人T解剖,而在中国,解剖人的尸体是违法的。很多著名的医生也只能靠去乱葬岗看被野狗咬破的尸体来研究人T结构,所以,怀疑对象就只有从西方国家来的医生,也只有你了!”
范穆尔把两手一摊,说:“您还是在推测,我要的是证据!”
张怀圣眨了眨眼睛,说:“物证,是你的手术刀,人证更简单,你知道,孩子是不会撒谎的,而你,却偏偏教你的女儿撒了谎!”
范穆尔像被迎头打了一拳,他急切地抓住了张怀圣的手,说:“您去找过我的女儿了?”
张怀圣点点头,说:“是,你不该让孩子牵扯进来,西城地方不大,要找一个小孩子本来不难,但这个孩子偏偏大家谁都没见过,这不奇怪吗?开始怀疑你之后,我到了教堂,很容易就打听到你有个女儿寄养在那里,当着上帝的面我问她,她什么都没有隐瞒,把你让她女扮男装去送信儿的事儿全告诉我了。范穆尔先生,现在整个案子里,我就有一点儿想不通——你为什么要这么做?”
范穆尔思忖了一会儿,长叹了一声,说:“我这样做,全都是因为您啊!只不过,我现在才明白,自己看走眼了!”
范穆尔告诉张怀圣,自己从英吉利回到大明,本来是想把英吉利比大明先进的一些东西传播过来,可没想到他在京城到处碰壁,毛遂自荐根本无门可入,投书谏议更是泥牛入海,不但受尽了冷眼抢白,还被人看成是头脑有毛病的怪人。最让他愤怒的是,在教堂里长大的张怀圣靠着视他如义子的刑部员外郎赵准关照,居然当上了刑部官员,虽然品级不高,却利用不少西方知识被人称为“神探”。而他这个从小接受正规英吉利教育的才子,却无人问津,因此他心里非常不平衡,这才想出了设圈套为难张怀圣的主意。
也是机缘巧合,前些天,范穆尔在野外看到了让他吃惊的一幕——屠夫霍进财因为煤气中毒已经死了,整个尸体都僵硬了,可人们不但不赶紧埋葬,反而将他用土埋住身子,晾在冰天雪地里。他曾经劝说搭棚看护尸体的人赶紧下葬,不料却被骂了一顿。作为家属的霍氏宁肯信鬼信神,也不肯信他的话,他心里气不过,又联想到对张怀圣的种种不服气,这才灵机一动,晚上偷了霍进财的尸体,将其手足和躯干上的肉剔出来,又用熟石膏将尸体填充好,放在车前面,自己坐在车棚里,趁天光未亮将尸块扔在了霍氏求过的四处地方。又伪造出霍进财驾车出城的假象,给张怀圣设计了一个解不开的“死套”,为了让这个“死套”更加完美,他又趁夜色将霍进财身上的一块肉偷偷放进杜猪儿的柴房,然后让女儿扮成小童儿的模样,去给霍氏送假消息,试图进一步把张怀圣引入歧途。至于霍进财的尸体,他已经找了一个隐秘的地方藏了起来。
听完范穆尔的讲述,张怀圣摇了摇头说:“范先生,让我说你什么好呢?为了和我一较高下,您居然偷偷破坏人家的尸体,还栽赃陷害,在大明律条里,这些都是可以判你死刑的!”
范穆尔不以为然地说:“我仅仅是解剖了一具尸体而已,我是医生,我有解剖尸体的权利,至于栽赃陷害,那也只是个智力游戏!”
张怀圣点了点头,拿起桌上摆着的一支香蕉,对范穆尔说:“范先生,不管你承认不承认,你现在已经是个香蕉人了,你虽然表面上看是汉人,但你的脑子和心都是英吉利的。你用英吉利人的眼光看待大明朝的刑律,那就大错特错了!”
范穆尔站起身来,把两只手背过去:“张怀圣,我彻底服您了,您带我回刑部治罪吧,不过我求您不要抓我的女儿,这件事跟她没有任何关系!”
张怀圣笑了笑,说:“这件事因你和我较真引起,我也有一定的责任,我看不如这样——今天晚上,你带着你的医疗器械,我带着那四块尸块出城,咱们找到霍进财的尸体,然后你将那尸体上的石膏敲掉,将尸块缝合回身上,再弄一口上等的棺木将其收殓,雇一辆马车送回城。其他的事情我来处理,如何?”
范穆尔冷冷地看着张怀圣,说:“我对大明失望,其中法纪不严就是很重要的一条,作为刑部官员,您执法都像儿戏一样,看起来大明真的没希望了。”
张怀圣笑着摇摇头:“非也,我并不是不处罚你,我已经想好了两条处罚你的办法,一是你到照磨所来,做我的助手,你的解剖技术对我研究案子非常有帮助;二是罚你行走乡间,好好学学中国的医术,将中西医的精髓结合起来,治好更多的病人。最主要的是,我不希望为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再搭上一条鲜活的生命,更不希望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失去她的父亲。”
范穆尔一把握住了张怀圣的手,说:“我选第二条惩罚,我要用我的后半辈子,来救赎我今天犯下的错误,让我变成白色的心,再变回黄色!”
张怀圣也伸出手去,两双大手,紧紧握在了一起……
七、诊所瞧病
一夜无话,第二天,张怀圣的风寒病又有些发作,严参扶着张怀圣上了车,刘庆吩咐车夫直接去城北神医堂,却被张怀圣拦住了,张怀圣让车夫赶奔西城。
刘庆和严参都愣住了:神医堂是京城最著名的医馆,里面还有从皇宫里出来的太医坐诊,而西城没听说过有什么著名的医馆啊!
马车来到西城,按着张怀圣的吩咐,左拐右拐,最终在离教堂不远的地方,他们找到了一间小门面,门口挂着一个金字招牌:范穆尔先生诊所。
刘庆一看就瞪大了眼睛,他转头朝车里问道:“大人,你要看西医?”
张怀圣从车里探出头来,说:“当然,我的风寒已经吃过好多剂中药了,至今难以痊愈,我想试试西医,而范穆尔先生的诊所,是京城唯一一家西医诊所,我跟他曾经有过一面之缘,也算是半个熟人了吧。”
刘庆和严参扶着张怀圣下了车,进了诊所。诊所的墙是白色的,桌子凳子也是白色的,里面冷冷清清,刘庆吸了一口冷气说:“大人,一看就知道这诊所生意好不了,到处都是白色,这可是病人最忌讳的颜色。”
正说着,一个穿白大褂的大夫从屋里走了出来,不用问,这就是范穆尔医生了。范穆尔四十岁左右年纪,瘦高个,眼睛不大却非常有神,见到张怀圣,他先是愣了一下,和张怀圣握了握手,示意张怀圣坐下,问起了张怀圣的病情。问完,让张怀圣解开扣子,凑近张怀圣的心脏听了听。旁边的刘庆扑哧一声笑了出来,转头对严参说:“老严,看到没?西医这玩意儿就是不行,幸亏咱们张大人是个男的,要是个女的来,他这么听,还不让人家丈夫打个一佛出世,二佛升天?”
张怀圣回头瞪了刘庆一眼,说:“别瞎嘀咕,中医是医学,西医也是医学!”
刘庆一吐舌头,不说话了。
范穆尔也不怪罪刘庆,他站起身,让张怀圣半躺在一张长椅上,随后拿来一个铁盒子,从里面拿出一个瓶子,用镊子从里面夹出一小块纱布,在张怀圣的右手腕涂抹了几下,随后又拿出一把跟手掌差不多长的亮晶晶的刀子,冲着张怀圣的手腕切了下去。
这下别说刘庆,连严参也不愿意了,两个人几乎同时跳了起来,一个挡在了张怀圣跟前,一个从后面抱住了范穆尔。范穆尔急得大叫起来,张怀圣连忙叫严参刘庆让开,告诉他俩不要惊慌:范穆尔先生并不是要伤害他,而是要对他采取放血疗法。
范穆尔点了点头,只见他轻轻切开张怀圣腕子上的一块皮肤,随即鲜红的血液就流了出来,过了一会儿,他用纱布将张怀圣的伤口包好,进屋拿出一杯红褐色的饮料,递给张怀圣,说:“喝了它,您就好了!”
刘庆一把夺过饮料,喝了一口,随即吐了出来:“这是什么东西,咸不咸苦不苦的?天下还有比这更难喝的东西吗?”
张怀圣从刘庆手里拿过杯子,一饮而尽,说:“你不懂,这是范穆尔先生自己配的药。”说完,他掏出银子付了诊金,在刘庆等人的搀扶下走了出来,上车回了照磨所。
一路上,刘庆不住地埋怨张怀圣:外来的和尚好念经,这个叫什么范穆尔的,哪里有个医生的样子?穿的衣服像个孝袍子,修的诊所像个停尸房,更可气的是治病的手法,跟杀猪有什么区别?
张怀圣听他说了“杀猪”两字,笑了:“刘胖子,你总算把话题绕到案子上来了!”
严参在一旁说道:“大人果然是胸怀锦绣,刚才范穆尔给你放血的时候,我仔细看过了,能把霍进财尸体分割得那么精细的,非范穆尔的手术刀莫属!”
刘庆这才恍然大悟,他急切地问:“大人,咱们为何不当场抓住他?”
张怀圣笑了笑,说:“你放心吧,他不会跑的,而且据我猜测,做分开这件事,他也许并没有恶意。”
回到照磨所,张怀圣把范穆尔的来历告诉了大家:他本来是大明的子民,十多年前,二十出头的范穆尔跟随父母到英吉利讨生活,三个月前才回到大明,去的时候,他还是做事毛毛糙糙的愣小伙儿,回来的时候,已经变成了一个百事通,他既能说中国话,也能说英吉利话,天文地理法律医学航海无所不通。因为都到教堂里做礼拜,张怀圣曾经跟他见过几面,两个人还为大明和英吉利谁更有希望争论过,结果谁都没能说服谁。
刘庆琢磨了一会儿,说:“大人,这件事我看还是按照无头案结了吧,再弄下去,我怕收不了场了!”
张怀圣却是胸有成竹,怎么收场,他已经想好了。